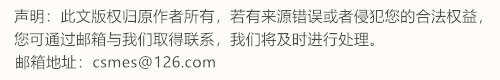在当今社会,音乐无处不在,音乐聆听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许多人认为,音乐聆听不仅能调节情绪,而且也有助于促进认知加工,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莫扎特效应”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让大学生分别聆听10分钟莫扎特钢琴奏鸣曲(K448)和放松指令,或静坐10分钟。结果显示,聆听莫扎特音乐后,大学生在空间推理测验的分数最高,而聆听放松指令和静坐后的空间推理测验分数没有明显差异,表明音乐聆听可以促进人们的空间推理能力。该研究1993年发表在Nature杂志上,随后产生了轰动效应,风靡全球。
在“莫扎特效应”研究中,音乐出现在认知加工之前,即强调在认知任务前聆听音乐。以这种方式呈现的音乐被称为先导音乐。与先导音乐不同,背景音乐则是音乐和认知任务同时出现。随着手机、电脑、iPad等媒介的日益普及,无论是在休闲还是在工作的时候,音乐时常伴随着我们。即便在学习的情境下,边听音乐边学习似乎已成为大多数学生的习惯,背景音乐被认为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途径之一。据调查,90%的人喜欢边听音乐边学习;约77%的学生相信,背景音乐会使他们学习更出色。一些研究发现,背景音乐可以促进和提升人们的认知水平(比如数字记忆、词汇记忆、语言理解等)。
问题是,无论聆听先导音乐,还是背景音乐,究竟如何促进认知加工?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不仅有助于优化音乐聆听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而且也有助于解释该领域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基于音乐在情绪表现和感染方面的突出作用,本文聚焦音乐情绪,围绕音乐情绪唤醒和奖赏两个方面,阐述音乐聆听对认知加工的影响机制。
通过唤起积极情感,音乐聆听可以提高认知加工
澳大利亚音乐心理学学家威廉姆斯·汤普森(William Forde Thompson)及其同事在2001年提出情绪唤醒假说(Mood—arousal hypothesis),该假说可以部分解释音乐聆听对认知加工的促进效应。其内涵是,音乐可以通过激发积极情感、提高唤醒水平,从而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在该研究中,被试聆听两类音乐:莫扎特与阿尔比诺尼音乐,其中,莫扎特音乐具有愉快情绪、富有动力性;阿尔比诺尼音乐则是慢速的,表达悲伤的情绪。结果显示,被试在聆听莫扎特音乐后,其空间测验成绩最高,而被试在聆听阿尔比诺尼音乐与安静条件下的空间测验成绩没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缘于,与阿尔比诺尼音乐相比,莫扎特音乐能诱发更多的积极情绪与更高的唤醒水平。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音乐对认知加工的促进效应有两个前提。
第一,听者必须能被音乐所感染,并体验音乐的情绪。众所周知,音乐可以表现情绪。通过声学要素(比如音高、音强、音色、速度等)与调式特征,音乐可以传达快乐、悲伤、生气等情绪。不仅如此,由于音乐具有强大的情绪感染力,它也可以影响听者的情绪。因此,从听者角度上说,音乐聆听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听者识别出音乐表达的情绪,但没有被这些情绪所感染。比如,听者知道音乐表达悲伤情绪,但是他并未感到悲伤;另一种情况是听者不仅可以识别出音乐表达的情绪,而且还会被这些情绪所感染。比如,听者识别出音乐表达悲伤情绪,且他也感受到这种悲伤。就情绪唤醒假说而言,听者的情绪唤醒是实现音乐聆听促进效应的前提之一。
第二,听者唤醒的情绪必须是积极的情绪,这是实现音乐聆听促进效应的另一个前提。从上述汤普森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两点:愉快音乐能诱发积极情绪,提高唤醒水平,使听者感到愉悦,由此促进随后的认知加工;如果音乐是负性情绪的,则听者难以从音乐中感受到积极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音乐聆听难以促进认知加工。可见,不同情绪的音乐诱发不同的感受,由此影响音乐聆听对认知加工的效应。上述两个前提可能可以解释,在先导音乐研究中,为什么一些研究未能复制出“莫扎特效应”的原因。
由于在“莫扎特效应”研究中,先导音乐出现在认知任务之前,二者是先后出现的。然而,在背景音乐研究中,音乐与认知任务同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背景音乐也能像先导音乐那样,诱发听者的积极情绪,提高他们的唤醒水平?
按照认知干扰假说(Distraction hypothesis),同时呈现的背景音乐将分散个体的注意力,从而降低个体的认知加工水平。该假说实质上是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在1973年提出的资源限制理论的延伸。卡内曼认为,虽然注意力可以同时分配给多项任务,但是注意力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任务所需的资源总和超过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则两种任务就可能发生相互干扰。比如,语言推理、阅读理解不仅涉及对字母辨认、语义通达等自动加工过程,还包括语义的精细化处理、语言生成等控制加工过程,因此需要占用较多的认知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背景音乐的出现将占用有限的认知资源,可能造成工作记忆的超载,从而表现出对语言加工的干扰效应。
然而,也有研究采用简单的或熟悉的音乐作为背景,发现背景音乐对语言加工具有促进作用。这可能因为,这些简单的或熟悉的背景音乐并未占用较多的注意资源,由此个体仍有足够的注意资源加工语言任务。因此,在2011年的研究中,澳大利亚音乐心理学学家威廉姆斯·汤普森(William Forde Thompson)及其同事认为,背景音乐既能通过情绪唤醒产生积极影响,也会由于占用注意资源产生消极影响。当这种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时,背景音乐就会有益于认知加工;当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时,背景音乐就会阻碍认知加工;而当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相互抵消时,背景音乐则对认知加工没有影响。的确,背景音乐对认知加工的影响效应不仅取决于特征、类型、风格等方面,而且还依赖于听者的人格特质与音乐偏好等个体因素。
通过获得奖赏,音乐聆听可以促进认知加工
音乐在唤起听者积极情绪的同时,也能带来奖赏。作为奖赏物,音乐与美食、金钱等不同,它是一种抽象的、内在的奖赏物,直接与愉悦体验相关。的确,聆听音乐令人愉悦。这种愉悦感实质上缘于音乐聆听中的奖赏预测错误,也就是说,当实际听到的比事先预测听到的音乐更好时,个体内在的愉悦感油然而生。这种愉悦感亦可诱发多巴胺的释放,激活大脑情绪和奖赏回路,比如,眶额皮层、扣带回、脑岛以及腹侧纹状体、杏仁核等。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加拿大心理学者欧内斯特·马斯—埃雷罗(Ernest Mas—Herrero)及其同事在2018年采用经颅磁刺激的神经调控方法,通过对左侧背外侧前额皮层施加磁刺激,让该部位的神经元产生兴奋或者抑制,由此探究该回路在音乐愉悦感获得以及动机(花钱购买音乐)中的作用。结果如下图所示,对于同一段歌曲,如果在大脑背外侧前额叶与纹状体回路(奖赏系统的重要脑区)施加兴奋性的磁刺激,那么被试体验到的愉悦程度会增加,且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这首歌曲;相反,当在该回路施加抑制性的磁刺激时,被试体验到的愉悦程度减少,且不愿意花钱购买该歌曲。这说明,大脑背外侧前额叶与纹状体回路的激活直接影响了人们从音乐中获得的愉悦感。
经颅磁刺激示意图。(其中蓝色圆点处是施加磁刺激的左侧背外侧前额皮层。)
奖赏诱发多巴胺的释放,而多巴胺在人类的记忆与学习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释放的多巴胺浓度与个体从音乐中体验到的愉悦感强度呈正相关。不仅如此,多巴胺还可以巩固音乐记忆。这是因为,人们从音乐体验到的愉悦感与记忆能力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听者从音乐中体验到的愉悦感越强烈,则他们对该音乐的记忆就越好。对于那些对音乐奖赏比较敏感的听者来说,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法国心理学者劳拉·费雷里(Laura Ferreri)及其同事在2020年发现,对于音乐奖赏敏感的听者来说,与服用多巴胺拮抗剂(利培酮)和安慰剂相比,服用多巴胺前体(左旋多巴)使他们在音乐聆听中体验到更强烈的愉悦感,且歌曲的记忆力也更好。该研究表明,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外在的强化物(多巴胺),而且也可以通过内在的、抽象的音乐奖赏提升记忆力。
奖赏能给个体带来行为或学习的动机,驱使学习的产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心情好的时候,人们就特别有动力学习或完成任务。这种奖赏学习被称为强化学习。它主要通过建立奖赏与刺激之间的联结,改变自身的行为,由此避免负性结果。研究发现,这种由强化学习建立的奖赏联结可以影响随后的认知加工,比如,习得的奖赏联结可以影响视觉注意的分配、调节冲突加工,而且还能影响面孔加工,甚至改善视觉工作记忆。
作为抽象的奖赏物,音乐的内在奖赏价值也可以直接转化为内在动机,由此促进强化学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在某个情境下听到某首乐曲,该乐曲让你特别感动。之后,你再次听到这首乐曲,当时的情境似乎历历在目。这是因为该乐曲的奖赏体验与当时的情境形成联结,无形中促进了该情境的记忆。
研究发现,通过聆听获得的音乐奖赏不仅能预测个体对音乐的长时记忆,而且也能促进非音乐刺激与音乐奖赏之间的联结学习。在特殊人群研究中,通过预先建立音乐奖赏与中性情绪面孔之间的联结,研究者发现,焦虑症患者能迅速地从负性情绪面孔中脱离出来,并将视线转向中性情绪面孔。因此,在治疗实践中,音乐也常被治疗师用作奖赏物,使个体通过强化学习,实现行为的改变或症状的减轻。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奖赏与学习的关系旨在维持特定的学习行为,那么,当奖赏物或奖赏体验消失之后,学习的动机可能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持续性的音乐奖赏刺激可能更为有效。从这一点上说,与先导音乐相比,合适的背景音乐可能对认知加工产生更为稳定和持久的促进作用。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无论对先导音乐,还是对背景音乐来说,音乐聆听对认知加工的促进效应本质上取决于听者是否从音乐中获得愉悦感,也就是说,音乐是否诱发了听者的愉悦情绪。但是,这个前提可能受制于个体的注意或认知资源:如果音乐聆听并未占用较多的注意或认知资源,则听者可能具备认知加工所需的注意或认知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音乐聆听就可能促进认知加工。
本文简要阐述了音乐聆听对认知加工的影响效应,然而,值得强调的是,音乐聆听与认知加工的关系较为复杂,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究,比如,情绪唤醒、愉悦感、注意等因素究竟如何协调作用?刺激属性和个体因素如何影响音乐聆听与认知加工的关系?等等。同时,本文聚焦音乐情绪进行论述,尚未涉及音乐聆听的其他方面(比如音乐想象、音乐记忆等)与认知加工的关系,因此,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最后,本文仅涉及音乐聆听,并未涉及音乐表演训练与认知加工的关系。尽管音乐聆听是音乐表演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音乐表演训练还涉及听觉—运动的整合能力。如何在音乐训练与认知加工关系的理论背景下,进一步深化音乐聆听对认知加工的影响效应的探索,这些都是未来研究需关注的问题。
0